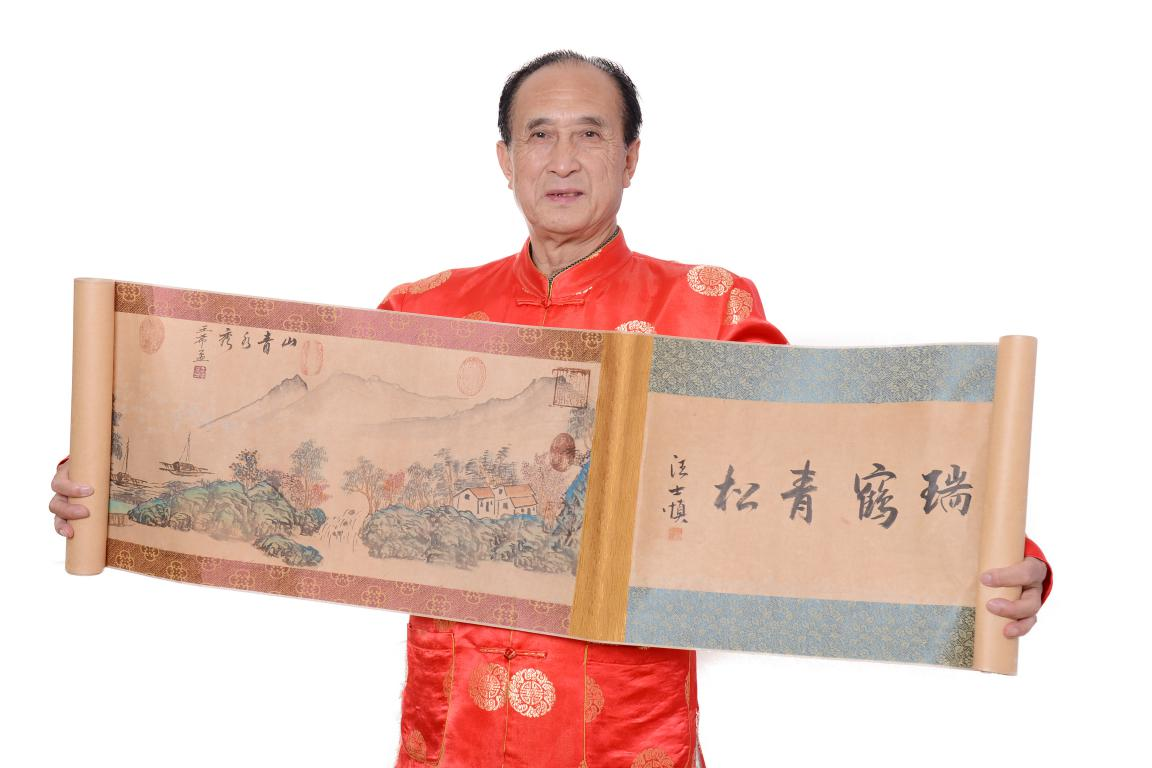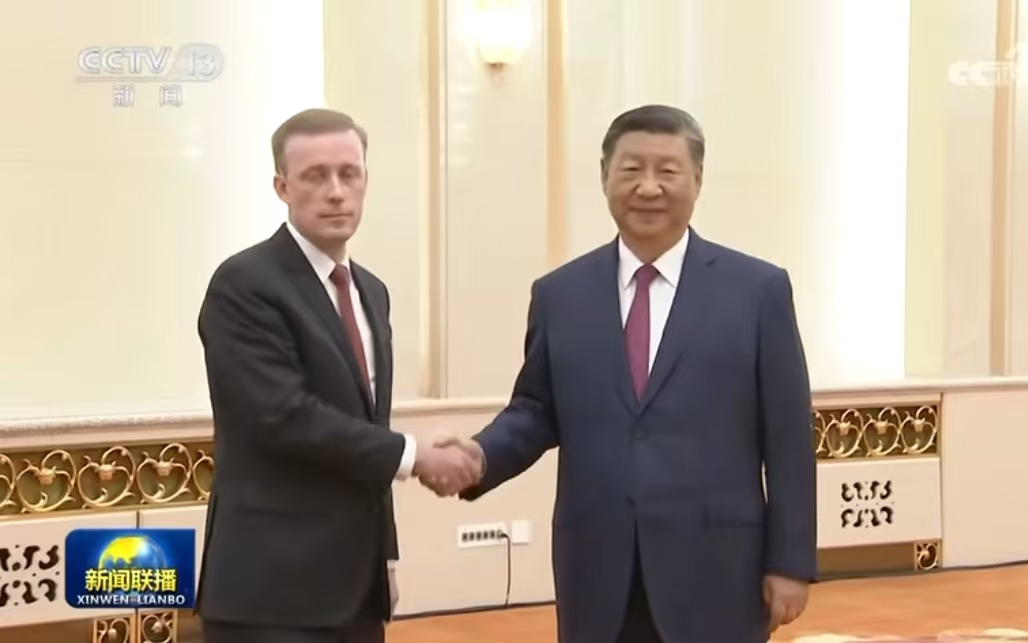玉见之美(节选)李玉刚 |
建盏
人世间的事情就是那么奇妙,充满各种因缘际会。
谁能想到呢,我之所以发心去进行这次文化之旅,居然是因为一只建盏的缘故。
2014年末,我发行了自己的第三张专辑《莲花》,这张原创专辑前前后后花了两年时间,有上百位艺术家参与制作,在台湾一经发行便引起轰动。主打歌《莲花》更是得到广泛的关注,因为曲风和我以往所有的作品都截然不同,充满着浓浓的禅意和放下自在的真实情感,所以坊间一直盛传李玉刚“了却红尘,皈依佛门”,李玉刚“出家”的新闻一度甚嚣尘上。
的确,我早已皈依佛门,但这和所谓的“出家”却是两回事。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中,我一直崇拜一位高僧——弘一法师。
弘一法师原名李叔同,出生于天津,39岁时在杭州虎跑寺出家,每次听到那首“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的经典旋律时,离别的愁绪和漂泊的过往便会涌上心头,令人不能自已。他圆寂时留下的那句“悲欣交集”,更是让我时常慨叹生命的无常和人世的变幻。
的确,把艺术视为生命的我,生活中时刻充满着感性,面对纷乱复杂的现实生活,出离的念头也经常萦绕于心。我一直寻找着心中的一方净土,到那里隐姓埋名,孤身而居。而彼时,一只“建盏”不经意间走进了我的生命。
那“建盏”来自一位出世的僧人,他是我的挚友。
那天他来到我的工作室和我探讨东方佛乐与西方唱诗班音乐的区别,我们又唱又跳,惬意极了。聊到尽兴时,他突然说:“我给你看一样东西,看你喜欢不喜欢。”
说完,便拿出一个小木盒,那只木盒子做得非常考究,散发着淡淡的香气,是用顶级金丝楠木制作。他小心翼翼打开木盒,里面现出一个麻布袋子,打开袋子,又是一层……就这样一层一层地剥离,最后,一只深褐色的、带着金属光晕的茶盏赫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真是绝美。”
我将茶盏捧在手里,仔细端详。
午后的阳光从工作室的窗户斜洒进来,温润的日光下,这只茶盏呈现出一种深沉内敛的气质,却又闪烁着斑斑点点的光芒,感觉神秘又不可捉摸,像极了我追求的舞台。我几乎按捺不住内心的狂喜,冒昧地脱口而出:“师父,这只碗真美,你能送给我吗?”
师父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却和我娓娓道出了这个茶盏的来历:
“这种盏叫‘建盏’,又称‘天目盏’,是宋代皇室喝茶的专用茶具,因为传世稀少,非常珍贵。在日本的正仓院藏有四只,被奉为国宝,并不轻易示人……机缘巧合下,我收藏了台湾艺术家的几只盏,这几只是当代建盏中的极品。”
两宋时期,饮茶方式由唐代的煎茶变为点茶,开始崇尚斗茶之风,时人对饮茶器具有了新的需求,在这种饮茶背景下,建窑的窑工们生产了一批批变幻莫测、绚丽多彩的黑釉瓷器。这些黑釉的瓷器,就是俗称的“建盏”。在宋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上至宫廷皇室,下至布衣之家,对建盏都有一种特殊的执迷,风靡一时。
而我当时手上捧着的那只建盏,就是一只来自宋代的油滴盏。
到底是什么让我对那只建盏一见倾心?后来我多次回忆起那天的光景。
在那段时间里,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迷茫。内心的挣扎非常强烈,经常会追问自己:这是你真正要的生活吗?每天披着明星的外衣,接受着别人对你的评判,不能自在出现于大庭广众,你的人生就要这个样子吗?
18岁离开家乡,一路奔波,最终成名,却也随即掉进了名与利的喧闹中。我本是一直喜爱安静之人,然而现在的生活和我的性格产生了极大的逆差。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经常会出现一些念头——等在山上的庙里,无尘世打扰,每日诵诵经,打扫打扫庭院,也许才是心满意足的生活。
或许终究是因为尘缘未了,也或许机缘还未成熟,念头过后,我仍在滚滚红尘中扮演着芸芸众生……
后来,师父当真把这只建盏送给了我。
确切地讲,是放在我这里保存,因为那只盏可谓是师父的传家之宝。它经历了千年的风雨,逃离了数次文化洗劫,最后传到了师父手上,无比珍贵。
师父说自己不会还俗,而珍宝的意义更多是在对文化的传承,也许放在我这里,是当下最好的归宿。
如今想来,正是因对这建盏的一见与一念,才令我踏上了访盏之旅,无意间却开启了一趟寻找大美中国的旅程。
隐匿山间的龙窑
建盏根据釉面图案的不同,大概可以分为三种:油滴、兔毫、鹧鸪斑。油滴建盏的釉面多是边缘不规则的结晶体,像油滴炸开,闪耀无比。兔毫建盏的釉面则是丝丝缕缕的结晶体,纤毫万千,淋漓毕现。鹧鸪斑顾名思义像鹧鸪鸟身上绚烂的斑点,结晶介于油滴和兔毫之间。
现在市面上的建盏,精品已经很少。
建窑创烧于唐末五代,盛于两宋及元初,元代中后期走向衰落。历史上建窑以烧造风格独特的建盏著称,尤以兔毫纹饮誉海内外。
在福建的建阳,如今还有很多制盏的工坊。这一次我们选择去往建阳的水吉镇,是因为那里的“龙窑”。
从武夷山开车到水吉镇,全程高速。坐在车内,望着窗外迅速闪过的山岭,我还略略感觉有些遗憾,这段到达宋代建盏的旅程,似乎缺了一些古意。1000年过去,宋代的风姿早已遥不可及,如今只能从书中的记载、画作的描摹,或者博物馆的文物中感受那一丝宋代的气韵了。
不觉中我进入了梦乡。在梦里,我竟变成了一个羽扇纶巾的公子,每天端着建盏,品茶论道,与友人下棋赋诗。
突然一阵猛烈的颠簸,一切烟消云散,我瞬间回到现实,抬眼间已到达了目的地。
几棵参天大树为我们遮住了炎炎烈日,三三两两的农房错落有致,村子四周是起伏的山坡,更远处则是连绵的山峰,远处的荷塘散发着诱人的清香,河沟边竟散落着很多瓷器的残片。此情此景,让我们一下子忘记了现实世界的喧嚣,心开始沉静,仿佛穿越回千年前的宋朝。
前来迎接的后进村村长赖敏惺告诉我们,建窑窑址主要分布在芦花坪、牛皮仑、大路后门和社长埂四处,方圆十数里,窑址总面积约12万平方米。早在晚唐五代时期,在芦花坪、牛皮仑等处窑址就已经开始生产青釉和酱青釉瓷器,器形以碗、碟、盏为主,此外,尚有执壶、盘口壶、罐、盒、盏托等。
厦门大学的师生和福建省博物馆的考古学者分别在六七十年代对建阳芦花坪窑址进行过两次发掘,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确定了“建盏是在龙窑中烧成的”,证明了“建盏的烧造年代创于北宋,盛于南宋及元初,而停烧或废烧于元末以后。特别重要的是发现了一批青黄釉器,证明建窑早在晚唐、五代迟至北宋,是烧制青瓷的地方”。
“你看,这里,这里,以及那边,”村长指着远处告诉我,“被野草覆盖的地方,曾经全部是窑口,地上随便一挖,都会挖到建盏的残片。一会儿如果不怕辛苦,我们可以爬到山那边去看。类似这样的龙窑,在当地有100多处,散落在各地,不单单是这一处。”
此刻,我们就站在了芦花坪窑址的门口。平时,窑址的大门是紧锁着的,打开曾藏有稀世珍宝的古窑址大门的钥匙,就在我身边这位看似貌不惊人的村长手中。
缓步走上通往古窑址大门的台阶,回首,是远方的连山和大片的荷塘。我的心里忽然一阵莫名的感慨和悸动。
门轰然打开,近千年历史的窑址出现在我们面前。
木头支柱,茅草搭的棚子,弯弯曲曲的窑口,仿佛千年间未曾改变。它一直向山坡上蔓延,大约有十几米长,因为它的身躯像是一条巨龙,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龙窑”。
“龙窑不像景德镇的窑口,景德镇的窑口形状像馒头,所以我们叫它馒头窑。”
130多米的龙窑窑口往往沿山坡而建,一层比一层高,这样,比较利于烟火往上蹿。
窑口里面,随处是残缺的陶钵。烧制建盏时,这些陶钵主要是被用来放建盏,上下各一,将建盏套在里面。建盏的珍贵在于,烧制成型的成品极少。当釉面的釉水在高温下流淌,会形成人为无可确定的或是油滴,或是兔毫,或是鹧鸪斑,或是曜变。脚下,已经几乎见不到建盏的残片,多是陶钵的残骸。对于茶人而言,就算是这些残旧破损的宋代陶钵,也是茶空间或者茶席上再好不过的装饰物,如果用来插花,则会精妙无比。
“这里是烧柴火的地方,那边也是烧柴火的。”村长指着一个半圆形的洞口说。这些烧柴火的地方,有的宽,有的窄,一层一层,根据地形的变化而变化。烧窑的时候,每层都要塞木头进去,否则整窑的温度上不去。用柴火烧窑,就是所谓的柴烧了。窑内的温度可以达到1300℃之高。柴烧的陶钵,会形成一层落灰,同陶土混合在一起,在高温下,形成别样的图案。
这个龙窑址只建了一半,村长说,估计当年是因为钱不够,而没有继续修建下去。这一类的窑口多为民间所有,资金跟不上,也是常有的事情。
这里每一个看似平常的场景都带着时间沉淀的质感,大片的富含氧化铁的黄土、残片举目皆是。它们仿佛还带着千年前的温度,尘埃中仿佛能听见烧窑人的笑声与叹息。在时光深处的烧窑身影、品玩建盏的皇帝和达官贵人们早已一并烟消云散。
我突然好奇,烧窑人自己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他们喜欢自己的生活吗?他们抗拒过自己的命运吗?他们是否也曾想过要走出这大山深处,跟着建盏一同去看看更辽阔的世界呢?
附近的村民仿佛自古都是从事烧窑或是参与建盏制作工作的。
“他们是不是祖祖辈辈都在做这样的事情?”我问同行的设计师陈旭,他喜欢喝茶,也喜欢建盏。
答案是否定的,“建盏已经断了800年,宋朝结束,大约元初时期,在兵荒马乱朝代更迭下,建盏慢慢便沉寂了。”
我一阵心痛,再美妙绝伦的东西,在历史和时光的长河中,也躲不过昙花一现的命运。
我忍不住躺在那些宋代残片上,感受着它们的低语倾诉。仿佛只有这样零距离的接触,才能释放和表达我此刻对那些匠人的敬意。
临离开,在窑址山门的左手边,我注意到,有两块黑色大理石碑,上面是建立古窑口遗址保护区时捐款人的名字,其中绝大多数竟然是日本人,只有寥寥三两个中国名字跻身其中。
原来,令我沉醉的建盏的风华,早已被大多国人忘却了。
残片与光阴
看完龙窑,我们决定去看村长刚才说的那些散落的老窑址。陈旭兴奋起来,说运气好的话,我们应该还能捡到一些老残片。
建盏的老残片,我想来竟也一阵激动。
后进村有1300多户人口,是山中一个安静的村落。每天晚上8点钟,这里就完全安静了。
莲子、水稻和竹荪是这里的主要农作物,村民过得倒也舒心安逸。
顾不上天气的炎热,我们一行人向着山野深处走去。
山路两侧尽是红薯地,些许的棉花田、稻田,以及大片的荷塘。沿途的橘子林向我们彰示着当地主打的水果。
我们的运气不错,走在前面的陈旭突然弯下腰去,捡起一片瓷片仔细端详起来,片刻后惊叫:“看!这就是宋建盏的残片!”我忙赶过去,看他的手掌心中那一小片方形的瓷片,拂去湿土后,竟魔术般呈现出幽暗的深蓝色,并能看出丝丝缕缕的线条,真正是典型的兔毫建盏残片!胎体很厚,却是薄薄的一层黑釉,如蓝墨一般深刻。
“从颜色看,这一片残片的时间应该是宋代早期,但建盏的顶峰时期是在南宋。”陈旭专注地盯着手里的瓷片说。
惊喜还在后面。走入草丛深处的小径,我们的双脚几乎等同于踩在了一条陶钵残片和建盏残片铺就的路上。同行的作家唐公子也是一位资深茶人,看到这些残片如获至宝。
我忙不迭弯下腰去捡起一片又一片的残片,不一会儿双手就捧了不少东西,喜形于色。
看到大家如此“贪婪”的模样,在前面带路的村长忍不住笑了:“一会儿回去,我还是给你们看看完整的建盏和陶钵吧!”
村长告诉我们,在建盏残片中,最珍贵的其实是油滴建盏的残片,因为数量极少,价值很高,现在一块油滴盏残片的价格也被炒到了一两千块钱。
而我们捡拾到的残片全是清一色的兔毫盏。当然,这一点都不影响大家捡拾残片的热情。
我们一行数人穿行于草间窄窄的泥巴路,越过一道水渠,再爬上一道山坡,拨开厚厚的长及腰部的杂草,一个巨大的坑口赫然出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村长刚才所说的“那个有树的山窝”了。由于被过度挖掘,它此刻更像是山间一个红色的裸露的伤口,让人觉得莫名哀伤。
残片从坑口一直铺到坑底,阳光下,密密麻麻,层层叠叠,如同断续的诗行。
“在这里捡拾残片是允许的,但是不可挖掘。”陈旭告诉我们,“随手拿起一片,可都是来自宋代的文物啊!”
建盏烧制,成品率低,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瑕疵,不完美的建盏是不能进入到宫廷的,又不能随意流落到民间,于是只有将它们就地打碎,这也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残片存在的原因。
“怎么这么多残片啊!太不可思议了!”唐公子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一个袋子,里面已经装满一路捡来的沉甸甸的陶钵和建盏残片了。
村长说,现在的地底下,应该还有好东西,但是至于有多少,那就不好说了。这里终究是已经被挖了二三十年了。
“现在想再挖已经不可能了,国家已经全部保护了起来,”他用手指着一片区域,“这里全部被保护起来了,国家要投资建立一个建盏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计划投资两个多亿。”
他感叹说:“再好的东西,也就是过过我们自己的手而已,人死了东西也不可能带到墓里去,过过手瘾,过过眼瘾,差不多就好了,总还是要给后人留一点。”
我望着村长的侧脸,一丝暖意在心中蔓延开来。
建盏风云
来到村长家里,我们终于可以坐下来,好好休息一下。
热情的村长招待我们喝茶。一边喝茶,一边讲起建盏的故事。
这里距离武夷山近,家家户户爱喝岩茶。对于当地人而言,喝茶是生活,与建盏打交道也是生活。
村长向我们展示他收藏的建盏。银毫、油滴、鹧鸪斑……大大小小十几只,在日光下闪烁幽幽微光。
眼看,手不动,是欣赏古物的规则。
在获得村长的许可后,我们按捺不住地终于拿起这些珍贵的物品,亲手触摸,感受它们的温度,感知千年前匠人的心意,似乎大家都想与它们进行一番心灵的对话,嘈杂的环境瞬间安静下来。
每一只都令我爱不释手,拿在手里来回摩挲,终究是经历了千年的时间,每一只盏摸起来都有着玉一般的温润,如同婴儿的肌肤。
村长讲起建盏的兴盛过往,简直信手拈来,就像是一部关于建盏的索引手册。
“最初的一轮建盏热是在1983年,外面的人进村子里来收,然后卖到广州,从广州再卖到香港去。一度,村民们承包当地的土地,不是为了种植庄稼,而是为了挖地下的老东西哦!”村长的可爱在于他的坦诚,“我也是挖过的,没办法!年轻的时候也不懂文物保护,而且那个时候家家户户都穷啊,穷到什么程度?连吃一块钱的饼都要欠账。”
像是讲电影老故事,往事在村长嘴里活灵活现,“我们都是和自己同村的好兄弟一起出去,各自拿着铁锹等工具,直奔老窑口。有的负责放风,有的负责挖掘。半夜开始行动,一看到远处有亮光,负责放风的人就小声喊:快跑喽!于是大家拿起东西,赶紧四散而逃,都是往山上跑。那个时候,抓住可是要坐牢的。”
村长点上一支烟,继续给我们讲述“建盏风云”,“后来严打的时候真不得了,连一个残片都是要被收走的哦!”他嘴里发出近乎哀叹的啧啧声,“国家派了武警看守窑口,白天黑夜巡逻。不过,武警一走掉,村民就想办法挖。没办法,那个时候没钱啊。尤其是晚上,带着手电筒上山挖。”
那一段时间里,仍然有广东人冒着风险来收老盏,穿着破凉鞋,挑着箩筐,假装是收鸭毛的,活像地下工作者。
村长指着面前的一只兔毫盏说:“1988年前后,像这样的一只老盏,底足无损坏,器形完整,价格可以卖到3000元到4000元。这个价格,在那时你们想想意味着什么。那时的台湾、日本以及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得好,大多数老盏最终都落入到他们的手里。也是在那个时候,一只老兔毫盏可以拍到30万港币。而现在,像那么完美的、几乎挑不出毛病的兔毫盏已经找不到了……”村长突然停顿了几秒,我注意到他眼中流露的一丝苦涩。
“那时候早,还能从窑里挖出来,现在已经不可能挖到了。那些形制完美的盏,早已经流落到私人手里,或者是国外了。别看网络上有那么多老盏的图片,但是,只有我们在这里的人才知道,上等的老盏究竟有多漂亮……”
村长说到了1990年、1991年,对建盏的需求突然出现了回落,甚至一度落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
“行情惨到什么程度?一只完美的老杯子,开价50块都没人要。现在的价格?一只开价在15万到20万,一点都不夸张,还不一定能买到。”村长感慨地说。
2003年开始,老盏行情略有回涨,稀稀落落开始有人来看货,都是古玩圈子里的人。价格也从几十块逐渐涨到几百块。低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2004年左右。后来随着经济的复苏,对建盏的热情又重新高涨起来,一直持续到现在。
“现在一个老的残片,尤其是油滴之类,可以卖到两三千块,原来的时候哪里有人要,漫山遍野都是。老盏被挖得越来越少啦!现在很多人会烧一些新盏来谋生活。”村长拿着一块粘着黏土的残片又陷入一阵沉默。
村长自己已经烧了7年的建盏,我们能感受到村长对建盏文化深沉的热爱。“村长现在成了建盏的代言人,在外界的识别度非常高呢!”陈旭打趣村长说,“我自己也在烧窑,村长烧的蓝釉我就特别喜欢。”
我们在村长家喝茶用的茶器茶具,无论茶杯、分茶汤用的公道杯,还是泡茶用的盖碗,都是清一色的建盏,当然,它们都是新的。
与内敛从容的老建盏相比,这些新的建盏都有着无一例外的明晃晃的亮光,气场外露,张扬得很。但是,如果放在茶席上,用来泡茶,由于整体色调的深沉,它们仍旧比一般的茶具更能压得住阵脚,显示一种不怒自威的霸气。
村长也在一直探索让新建盏更具内涵的方法,他尝试把老陶钵上的垫饼和新建盏的制作融合在一起,以其作为新建盏的杯底。这样烧出的东西,有新有旧,有过往有现在,混在一起能彰显出特别的魅力。
“我还打算做几个柴窑,用柴窑烧出的东西和用电窑烧的东西釉面不一样,更有质感。”
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创意,我们都被他的想法触动了。
曾一直认为,做文化创意的事情,一定要打破传统的观念。而现在想想,垫饼尽管是土质,毕竟也是千年前的宋物,不有效加以利用,往往成为受人忽略的存在。如果善加利用,它的时间价值便会在器物上彰显出来,为新建盏平添几分厚重的气息。
我对建盏之所以情有独钟,是因为它代表了宋代文人的一种独特的精神境界。建盏的颜色相对纯粹,偏褐色、黑色,或者是暗蓝色、黄红色、黑蓝色,不会在上面人为地画一些花草之类,而是全凭借烧制的工艺取胜。它呈现一种近乎素朴、幽玄,甚至是高古的美感,仿佛遗世而独立的隐者。
建盏烧成不易,烧制过程更是危机四伏,比如,温度太高不行,釉水会和胎滴粘在一起。或者,胎土因为高温而坍塌掉,和其他的盏粘在一起。随时会有各种瑕疵出现,防不胜防。村长收藏的一只鹧鸪斑老盏,整个器形非常漂亮,但是,美中不足,有几处的釉水在烧制中产生了凝结,略略致残。所以,古人对建盏的欣赏,往往也是抱着“心随万境转,转处实能幽。随流识得性,无喜亦无忧”的心境。
建盏美则美矣,对于建盏文化的传承传播,却是任重而道远。
初尝制盏
与村长喝完茶,我们便离开宁静的后进村,驱车直往建阳。
从后进村到建阳的路途有些遥远,尽管全程都是高速公路,我们也开了将近一个小时。
这一次,我们是要去探访年轻匠人陈旭的建盏工作室。
在村长家里,我们分享了建盏的风云往事,赏玩了老建盏。然而作为更年轻的一代人,有志向的陈旭给我们一行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充满朝气的他,对于建盏不知又有着怎样的执著与理解。
“一旦钻进去,建盏确实会让人痴迷啊!”在车里,陈旭这样告诉我。他自己也收藏了一小部分宋代建盏,“价格太高了,只能少收一点玩玩而已。”
作为80后的一代人,陈旭出生于茶叶世家,父辈都是做茶出身。2000年的时候,他自己开始经营茶叶生意,在这个过程中,逐渐了解到茶器对于饮茶的重要性。作为建阳当地人,陈旭在选择经营茶器的时候顺理成章地选择了建盏。2010年开始,陈旭把建盏纳入到自己的经营体系中来,再后来,干脆创建了自己的建盏工作室。
一方面是兴趣,一方面是工作的需要,陈旭陆陆续续收藏了近百只建盏,以珍稀的藏器为主,另外就是一部分具有独特性的标本性建盏。“器形完整的老建盏现在价格太高,而且也已经不好进行买卖了。”
在他看来,建盏的美感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古朴,内敛,因为颜色单一,反而更耐看。从喝茶的角度讲,低调的建盏放在茶席上不抢眼,不会夺茶的风头。即便作为单独的摆设品,也会让人感觉舒服。
建盏的审美因人而异,因角度而异。有人爱看兔毫或者是油滴的肌理,仿佛观看一幅油画。对禅学感兴趣的人,在喝茶的时候,在一杯茶汤中,从建盏的斑点和纹路,仿佛会悟到禅宗的奥义。
谈话间,我们到达了此行的目的地。
在陈旭工作室的泥料池内,整齐码着建盏制作需要的三种泥料:田土、瓷土和红土。田土可塑性高,瓷土耐高温,红土则是含铁量比较高。不同的泥土配比,会对釉面的形成产生不同影响。
我在陈旭工作室内,体验了一把做建盏拉坯的感觉。由于此前我在景德镇自己也拉过坯,所以在这里上手倒也不觉得陌生。拉坯是成型的过程,坯要拉好,泥巴首先要揉均匀。
我的心得是,拉坯的奥妙在于拉的过程中,轴心要稳,双手要把泥巴抱正,拉出自己想要的器形来。器形要拉到位,需要一定的审美,另外就是经验的积累了。熟能生巧,确实是真谛。
拉完坯,我还体验了一下装窑的感觉,戴上手套,用长镊子把制作成型上好釉的建盏送到窑里去。
对于现代人而言,建盏的制作工艺,仿佛是一个谜一样的存在。
建盏的整个制作环节同一般的瓷器制作大致相同,而主要的差异性体现在烧窑方面。在窑内,所处的位置不一样,温度也不一样,形成的颜色与图案也便不尽相同,这就是所谓的烧窑气氛。
建盏烧制的难度在于,哪怕它的温度相差两摄氏度,烧出来的颜色也会有差异,而青花相差20℃左右才会有些颜色的差异。所以,建盏的成瓷率极低。
陈旭进一步解释说,建盏温度相差小而颜色有大的差异的原因,是由于胎体中的铁元素比较活跃的缘故。在窑变的作用下,胎土矿物质中的三氧化二铁会随着不同的温度呈现出不同的美感。
1280℃和1281℃,尽管只差一度,但是如果保温时间相差哪怕三五分钟,建盏的颜色便会有差异。所以,烧建盏就是,一窑出来,什么颜色都有。
所以,很大意义上,建盏的美在于它的不可测的变化性。
建盏虽一度中断失传,但经过岁月的洗礼,终究以自己独特的魅力被人们重新仰视,虽然现在还远达不到当年的制盏工艺,但这些默默守护、传承着建盏文化的人们,足以令人欣慰。
而我作为一个热爱传统文化的践行者,也初尝到了肩上承担的重任。
(《玉见之美》,李玉刚著,作家出版社2016年10月出版)
凤凰新闻社【责任编辑 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