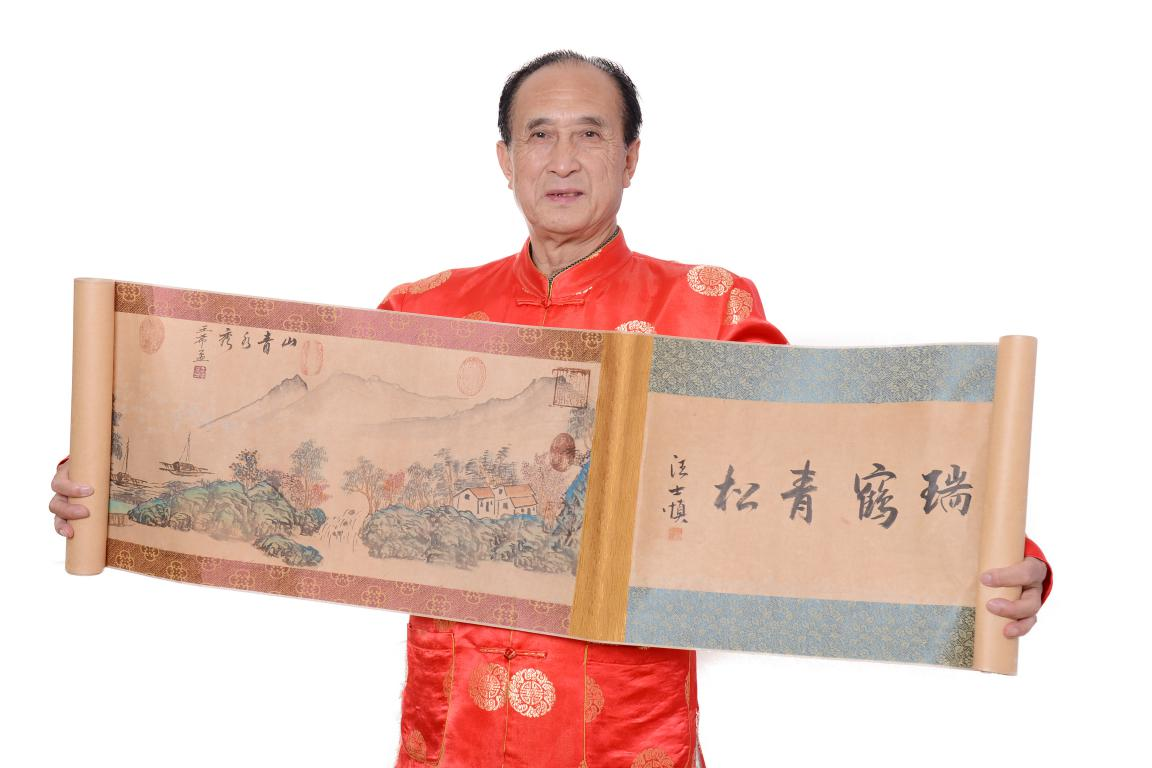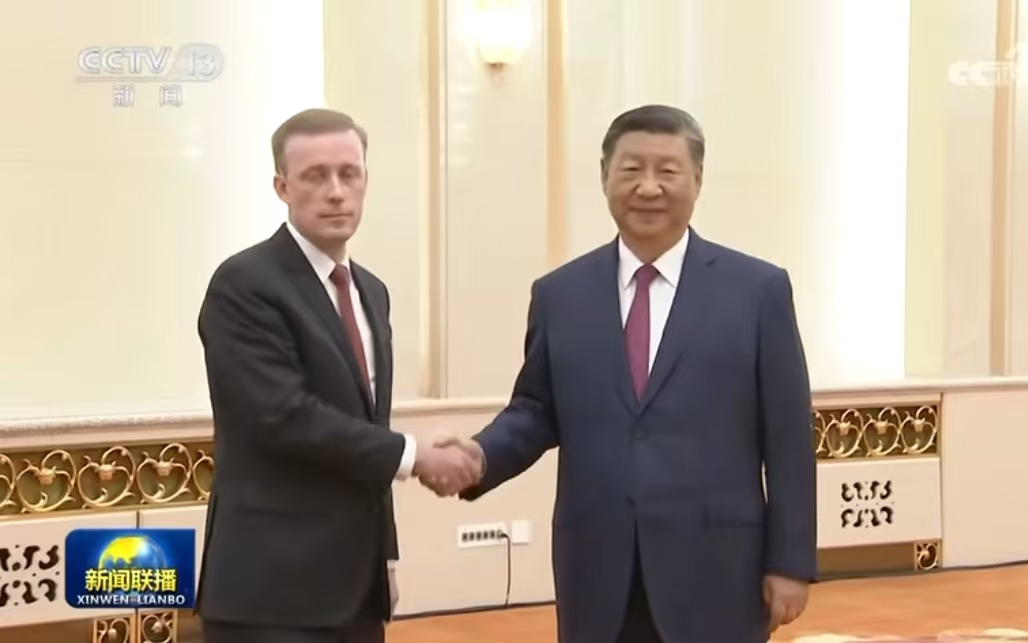草创时代的思想家大都有一种苦行色彩。苦行的极端化,即为宗教。章太炎认为,“墨家固然近宗教”,但是墨家最终未能成为宗教,儒学也如此。儒学不是宗教,孔子是一位随时可以出仕的政治家,一位诲人不倦的教育家,一位上溯民族文化历史、把握文化脉搏,下启人文精神、确立东方文脉的思想家。但是孔子思想中也有些类似宗教的因素,如其苦行色彩和悲悯情怀,这是儒学思想中最接近宗教的一种精神特质。

马克思·韦伯(图源于网络)
儒学虽然频频被后人力推为“教”,但儒学与“教”相去甚远。马克思·韦伯撰《儒教与道教》,硬伤很多但影响很大;杜维明为国外某出版社策划的《Our Religions 》一书撰写题为《儒教》一文,后来独立成册。但杜维明本人并不认为儒学为“教”,正文中亦多称儒学而不称儒教。因此,不难想象,杜维明撰写此书,无非不想放过一个很不错的给西方介绍中国思想的机会而已,不等于承认儒学是一种宗教。

杜维明(图源于网络)
儒学宗教化运动主要在民间进行。东南亚华人世界也有儒学宗教化的努力。但他们除了祭孔、拜孔之外,没有找到更好的让儒学宗教化的方式。1978年,任继愈在某论坛发表儒教是宗教的演讲,此后又就此命题多次发表演讲和文章,试图论证儒教是宗教。然而应者寥寥,只有少数学者如何光沪、赖永海、谢谦、李申等人相继以不同方式公开支持“儒教”之说。唐君毅论人文精神重建,却以西方经验为标本,认为宗教生活必需,这与儒学似乎有悖逆之处。美国汉学家安乐哲认为,“古典儒学既是无神论的,又具有深刻的宗教性,两方面同时兼而有之。这是一种没有上帝的宗教,是一种肯定人类自身的宗教。”安乐哲对于儒学宗教性的阐释,有一个西方色彩较浓的文化视野,比如孔子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这样的思想,被理解为“协同创造”,被与查拉图斯特拉“如果已有诸神,那末创世又意味着什么呢”式的思想并论; 又如,儒学的家庭,被当成一种宗教意味的隐喻,将家庭关系提升到中心地位,其意图在于将人的整个身心毫不保留地投入到他的每一个行动中;总之,对于古典儒学而言,“宗教性”从其根本意义上看,是指一个人清楚、充分地体悟到整个领域中现存事物的复杂的意义和价值,通过内省的觉悟,产生敬畏之心而获得的。
我们姑且不去质疑安乐哲对经典儒学的宗教含义的推衍的学理上的可靠性,而且安乐哲将儒学理解成“没有上帝的宗教”,看起来还是十分有创见的。但在这里,我们更倾向于用一种朴素的判断方法,去对于孔子思想中最本原的宗教因素进行简单的判断。因此,对于孔子思想富有宗教意味的成分,目前我们认为主要还是前面提及的两点:其一是苦行色彩,其二为悲悯情怀。做这样一种判断,首先居于一种相对狭义的宗教定义,其次,是在暂且不去对孔子思想作进一步推衍的情况下作出的判断。

傅斯年(图源于网络)
纵观孔子的苦行,并非主动寻求苦难,而是居于对苦难的蔑视和对“道”的憧憬,是一种主动的、不否定另一方价值的选择。同时,孔子的苦行也是有限的,并非绝对的殉道者。这是孔子苦行色彩与宗教苦行完全不同、最终没有走向宗教之所在。唐君毅论墨子之所以没能成为宗教,是因为“墨子畅言天志而期于实用,向往超世之情不著,终未能成宗教。”而傅斯年认为,“儒者以为凡事皆有差等,皆有分际,故无可无不可。在高贤尚不免于妥协之过,在下流则全成伪君子而已。这样的不绝对主张,正是儒者不能成为宗教的主因,虽有些自造法度,但信仰无主,不吸收下层民众,故只能随人均为抑扬”。傅斯年以成为宗教为标准,对于儒家的指责,道理并不充分。孔子思想没有走向宗教,更主要的原因当在对自身的定位,即一个清醒的人文主义者,孟子亦是如此,所谓“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并没有必定劝服人间世的诉求,因此也就无有殉道的期望,所谓“向往超世之情不著”。
孔子思想中另一种具有宗教色彩的因素,即悲悯情怀。孔子思想核心为“仁”,“仁者爱人”,整个“仁”论,其原动力为悲悯情怀。后世对“仁”有多种解释,孟子所为“恻隐之心”,将“仁”具体化。但这种情怀亦止步于人文主义者的应有的尺度,没有把自己打扮成为救世主,没有传递超然之音,没有表现出超越个人能力的神奇力量。各种可能导向超然的情感,在一个人文主义者不语怪力乱神的话语中,归属于世俗,归宿于凡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