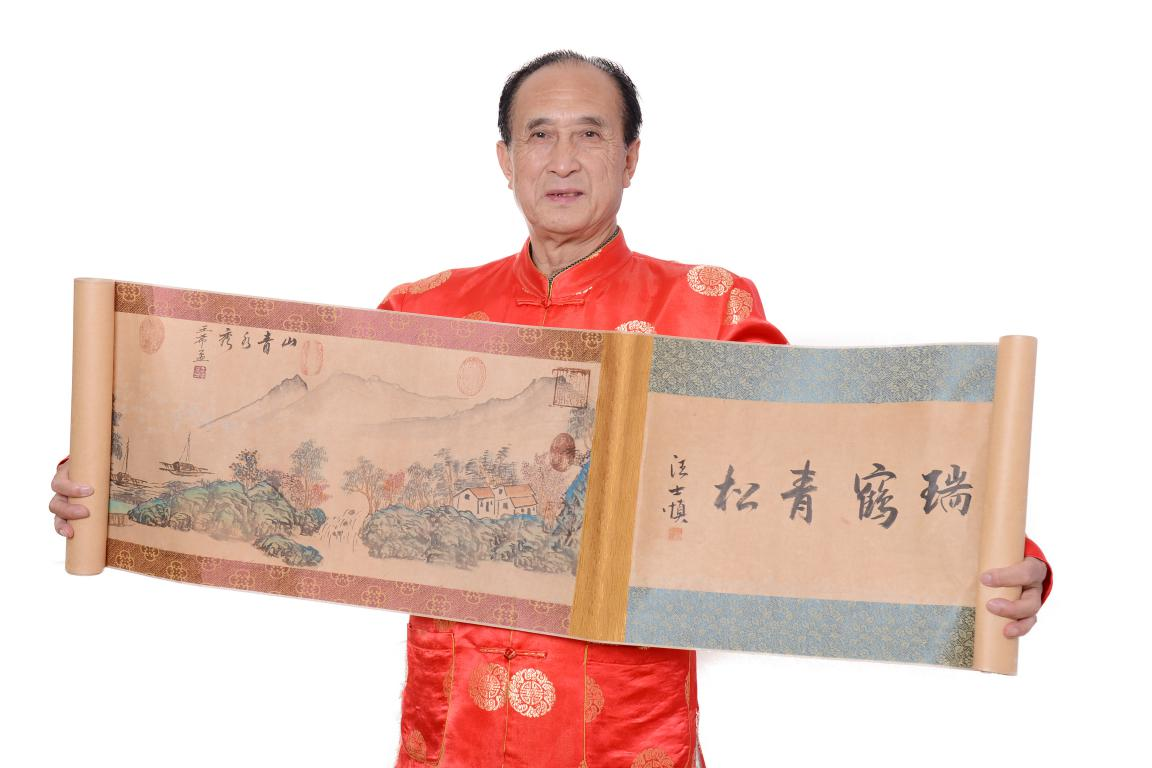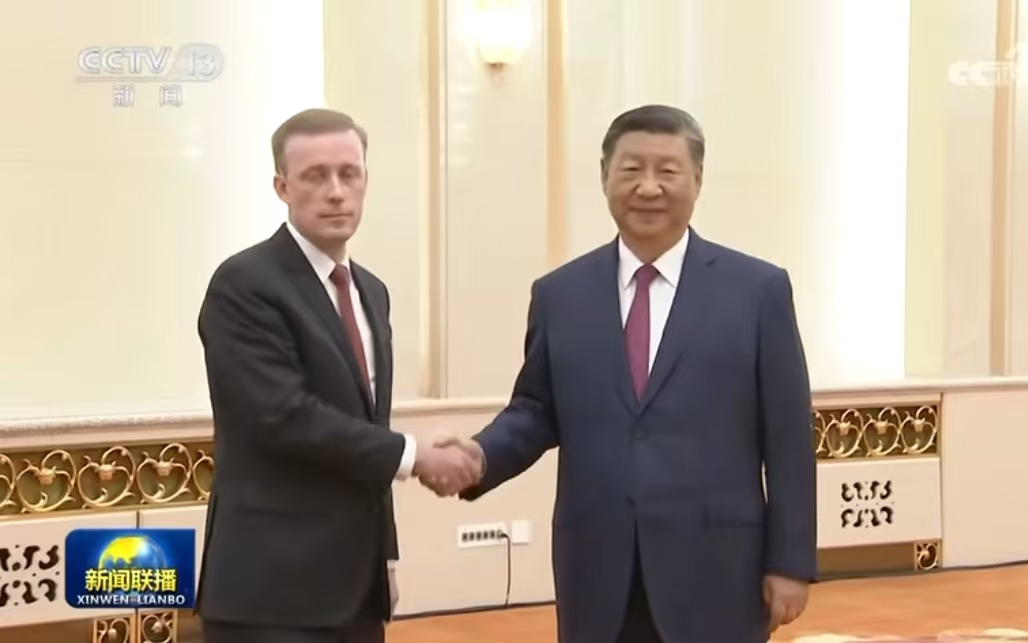回家,陪爸爸过年
凤凰新闻社【空谷幽兰/文】

作者 空谷幽兰
“妹妹,爸这次病得厉害,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电话是哥哥从老家打来的。
听到消息时,正值春运高峰期,票也买不上。如何是好?“不行,我必须回去”。哪怕去车站给人磕头也要弄到票回去。我草草的收拾好简单的行李,带上女儿匆匆的准备赶回四川老家。
老公的表妹得知后,赶忙在太原铁路找了一个熟人帮忙买票,实在弄不上就叫人先送上车再说。
我所在县城到太原坐汽车要四个小时左右。到了太原火车站,人潮如海。三五成群的人发出票涨价也买不上的叹息。一个高个子“黄牛”青年手里扬着几张票高声吆喝着。
我按照表妹电话里里的吩咐,在火车站后院铁路办公室找到了张局长。“你们母女俩先坐下,这不是正春运吗,票前半个多月就卖光了,我打电话托人在想办法,万一买不上就送你们先上车”。张局长说。
“谢谢张局长,给添麻烦了,大中午的耽搁你午休了”。我勉强挤出一点笑容说。
从门外急急匆匆走进一个穿铁路制服的女人气喘嘘嘘的说:“张局长,实在没法了,好不容易从票贩那里抢过一张卧铺,再买张站台票吧!”

“大姐,能不能帮忙弄两张硬坐啊,无座的也行,我女儿第一坐火车,我要和孩子一起”。秧求着。心里一边盘算着身上仅有的三百元。从家里走的比较急,老公叫我先去,他在家想办法再给打过去。
“妹子啊,这一张硬卧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抢到手的。再搞张站台票就可以上车”。这位大姐认真的说。张局长也在一边点了点头。没别的办法只有先上车再说,当天可以走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我吩咐了女儿一大堆话后,在车站人员的帮助下,母女各自上车了。我在七号车厢,找了一处人稍微少一点的地方站住了,准备车启动再补票。人流稳定些再去找女儿。
“喂,上车了吗?带好孩子,路上要多喝水”。是老公打来的电话。
“已经坐车上了,你也记得自己照顾好自己,不要上火,我挂了哈。”回答道。我一刚到太原站就用善意的谎言给老公发了条短信:“老公,人家把票给买好了,还有坐位。有熟人就是好,你放心吧!过年你也不能委屈自己,该吃啥就吃啥。”
我正准备到卧铺车厢找女儿,从八号车厢挤来一群人,身披彩带堵了个水泄不通。他们是搞春运期间列车宣传的。大声唱着《常回家看看》。旅客们高兴的鼓起掌一起哼着。回家的喜悦洋溢在脸上。“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听得我心在流血。此时,没有一个人知道我的心境。抬头望窗外,思绪在何方,要知心头事,谁知吾境况。
不经意间,一位漂亮的女主持人拿着太原电视台金话筒走到我面前,我只在电视里见过这情景。可能主持人见別人又是唱又是鼓掌的,只有我闲着,就选择采访。“美女你好,我们在做一个春运调查,想采访下您,谢谢支持”。美女主持对我说。

“实在对不起,主持人,我今天心情特别不好,讲话会语无伦次,你采访其他旅客吧!”主持人微笑着朝另一位男士走去。
一阵欢呼终于告一段落。我向卧铺车厢走去,被一位列车员拦住。“这是卧铺车厢,不能进。”我给这姑娘说了一火车皮的好话,还是不管用。“要不你帮我把我女儿去找来?她第一坐火车我不放心”。我说了女儿的特征,列车服务员还是铁青着脸说不行。这时,又过来一个列车服务员。这姑娘个子不高,看上去很和善。我把情况又向这位姑娘说了一遍。
“姐,你先別急,我给你叫去”。姑娘说着转身离去。我心里高兴,这回遇见好人了。过了一会儿,服务员一个人走了回来。“姐,没人啊!我喊也不答应。”列车员说。“这怎么可能呢,我送上车的啊。”我着急了。“姐,你先别着急,我用广播呼下”。说完转身走了。
“请豆豆注意、请豆豆注意,听到广播后,速到七号车厢,你妈妈在找你”。我听到广播的寻人消息,还觉得丢面子。原来是虚惊一场,由于早上赶车起的早,豆豆在上铺早睡着了。她睡梦中听见广播在呼叫,费了好大的劲到了七号车厢。
“豆豆看见我,一头扎进怀里。我激动的对列车服务员说:“妹妹,谢谢你啊!”。“姐,不必客气,我叫杜小风,有什么事尽管找我 。”哦,对了,姐,我给你补办理了一张卧铺票,再过八个多小时就可以坐卧铺。就可以和女儿在一起了”。列车员说。
“妹妹,谢谢你!这样吧,帮我换成两张硬张,无座也没关系的。卧铺里面空气不流通,太闷”。我非常感谢这位好心的服务员。其实是不舍得花钱,再买张卧铺就只剩几元钱了。
小杜折中了一下。把我领进了她的值班室,里面可以坐两人,白天豆豆可以到值班室来陪我。小杜怕领导看见,吩咐我把门关上安心休息。
哐当当、哐当当,坐了一天两夜的火车,我归心似箭,头又痛,快要崩溃了。不知道家父现在的情况怎样。
列车还没进四川雁门关隧道,不幸的消息就传来了。“妹妹,爸已经走了,我们现正在烧爸床上的用品”。电话是大姐打来的。我的眼泪不由自主的滚落而下。我想起最后一次见到爸爸时,爸爸的背已经驼了,不像从前那样矫健,军人的风姿已经不在,没想到这就是永别。我怕旅客看见,脸始终望着窗外,泪水在眼里打转,嘴上呢喃着:“爸爸啊,您为什么就不能再坚持一下,等等你远在他乡的孩子呢。”
“妹妹你到哪里了?村干部在催促赶紧火化,我说等你回来就马上办”。哥哥又打来了电话。“必须等我回来,如果村干部强行火化了,我回去杀了他全家”。我带着哭腔咆哮着对着哥哥说。
“妈妈你別哭啊!爸爸就是怕你路上有什么问题,叫我跟上保护你的”。女儿豆豆哭着用手抹去我腮边的泪。
下了车,故乡的年味满街都是,大街小巷挂满了红红的灯笼。时不时有几声小孩子玩耍放的鞭炮声。
我和女儿直接去了火葬场。村干部和亲戚朋友们也在那里等了好久,我一头扎进父亲身边,抓住父亲冰冷的双手撕心裂肺的哭喊着。“爸爸,您为什么不等等你女儿啊!”
“妹妹,这是自然规律,想开些,再等几十年我们都是要走的”。哥哥劝说着。
姐姐们把我拉开,眼睁睁的看着父亲用一台机器从圆洞输入了进去。出来成了一堆淡白色的灰。我和姐姐们再次泣不成声的叫着“爸爸,爸爸”。

我从窗口取出父亲的骨灰,轻轻的装进骨灰盒,再用红布包裹着。我止住了哭声,用手捧着红布包裹着的,热乎乎父亲的骨灰。紧紧的把它帖在胸口。感到父亲的骨灰穿透了我的胸膛,这是父亲给予自己最后的温暖。
泪眼婆娑中,我仿佛又看到了父亲期盼消瘦的脸颊。前额深深的皱纹,盼女儿归来的眼神。“爸爸,我接你回家吧,让妈妈再摸摸你最后的体温” 。“爸爸啊,您知道吗?你丢下妈妈一个人她会不习惯的”。“爸爸,你一路走好,恕女儿不孝,没尽孝道,就让女儿的每一滴泪化作一缕阳光,给您照亮通往天堂的路。”
恍惚中,远处传来三两声爆竹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股硝烟味。原来,年二十九到了。
责任编辑 檄文